作者简介:
张金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2012级本科生,国合记者团中文组前主编,记者。2015年2月至6月到阿曼卡布斯苏丹大学交流学习。

在位时间最长的阿拉伯领导人,深受爱戴的苏丹已执政近46年,仿佛在生动诠释着“克里斯玛”这个词的含义;气温40℃,在男女似乎泾渭分明永不相交的黑白二色洪流中,一个奇装异服的我在吸引大量瞩目的同时也在观察着这环境。

卡布斯大学一角
这是一篇已经拖了至少一年零一个月的随笔。
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仿佛有除了懒以外的理由。相较于当年以色列之行的惊心动魄(见本公众号《以色列札记——战火边缘的魔幻现实》一文),在阿曼的三个多月显得过于平淡,泛不起一丝波澜,终日便是靠校车在学校宿舍之间两点一线。步行所能及之处只有小商店聊供生活所需,稍大些的商业中心在十几公里之外。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假日里,只好惆怅地从窗缝里瞪视着旷野,努力用空调嗡动的噪声压制户外的热气和隔壁楼传来叮叮当当的装修声。
说到热——

现今记忆里对那段日子仅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就是“热”
腊月二十九凌晨从首都机场出发,十几个小时后迎接身穿羽绒服的我们的是马斯喀特高达35℃的热浪,我顿时被迫对接下来三个多月的生存状况做了一番重新估计。而车窗外掠过的不见一个行人的街道、罕有人烟的公路、有如电影里西部旷野一样的满眼砂石,又浇灭了我“徒步探索陌生地域”的热情。
学姐说,到四月份就开始热了。四月的第一天,热浪如期而至,猛然升温5摄氏度进入每天四十度时代。于是学校空调开始发威,室外40+℃,室内18℃,我每天都在疑惑到底应该穿什么。
一日,某老师嫌空调开得太低,遂问同学们,你们不冷么?同学答曰,冷。然后,老师把教室门推开了……
门,推开了……
热浪扑面而来。嗯,这下不冷了。

作者于沙漠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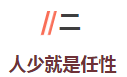
第一天,来接机的学校司机一手扶方向盘一手发信息,还不时180度扭头聊天的功夫着实把我吓得不轻。我费了一番努力才适应了他们边开车边看视频、回头说话、分发饮料、从各种匪夷所思的地方翻找东西的日常。
对于从小一直生活在中国人口千万级以上城市的我来讲,这个面积略大于两个山东省、本国人口没海淀区多的国家的确空旷得过分。每当我自我介绍“我来自中国首都北京附近一个人口一千多万的小城市”时,围观群众的脸上都异彩纷呈。
相对于国家人口来讲,公路里程和宽度令人称道,简直随处都可上演飙车大戏。马斯喀特市内快速路上车速轻松便可突破三位数——因街道通常车少人少,一旦车速低于20km/h司机们便开始大声抱怨堵车。
然而家家有车的副作用是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要去学校只能靠校车,想出行就只能站在公路边的砂石堆上翘首期盼一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即使来了也没有计程表这种东西全靠自己和司机讲价”的出租车。不过,当你顶着烈日/深更半夜在空旷的公路旁试图等出租车时,也会偶尔有当地人停下,顺路的话他们会很乐意捎上一程。
这个实例教育我们,一定要先抱一个当地有车一族的大腿。
同样由于本国人少,建设基本靠外国劳工。烈日炎炎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裔工人挥汗如雨挖坑刨土埋管道,本国工头身穿洁白长袍偶尔施施然视察一圈指示一番之后,回到屋里继续吹空调。

位于马斯喀特的卡布斯大清真寺

走在校园里,人群泾渭分明地分成了黑白二色:学校规定男生须着白袍戴小帽或缠头巾,女生着黑袍戴头巾——尽管有个别彰显自我者硬要穿彩色袍子上学。男女生使用分开的走廊和楼梯、分开的体育馆、分开的图书馆阅读区,在不同时间段使用公共娱乐设施。因此,从某楼一层走到二十米开外相邻并有走廊连接的另一栋楼一层的标准方式是:爬女生专用楼梯上二楼——沿女生专用的走廊,混迹在一群黑袍之中行进——下楼,到达目的地。路程约为直线路线三倍。
而且女生似乎在刻意同男生拉开某种距离。教室里学生坐成黑白分明的两群,即使屋内已经人满为患,靠近对方的那一排桌椅也往往无人问津,新来者宁可搬着椅子挤作一团,也不愿深入“敌营”,仿佛那犯了某种禁忌。
于是在那永不相交的两条洪流中,我这样一个“奇装异服”又抛头露面的外国人有如一个噪点,游移在黑白之间,获得了珍稀动物一般的关注度,经常出现有人跑到我面前“哎我在某某地见过你”然后我一脸懵逼地心想其实在我看来你们长得都一样的窘况。
到了阿曼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克里斯玛(charisma)”。由于卡布斯自上世纪70年代夺位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引领国家走向了现代化,极大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人民对苏丹充满着朴素而深挚的爱戴之情。所有政府机构、公共场合和许多人家里到处悬挂着卡布斯各式肖像。卡布斯之前因健康问题在德国治疗八个月,国内暗暗担心。归国当天,消息传来,集市附近交通忽然瘫痪,司机纷纷鸣笛庆贺,有人当街感动到痛哭,全国上下激动万分举行了大小庆祝游行,国内电话免费一天,简直比国庆节还热闹。
卡布斯大学内组织游行当天,我去围观了盛况。文学生、理学生、医学生,本国学生、外国学生戴着国旗配色的围巾,挥舞着发放的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国旗,举着绘有卡布斯像的立牌,甚至有人带来了专门制作的帽子,浩浩荡荡行进在学校主路上,绕校园一周(通常完成此路程需要乘坐校内摆渡车),终点是稍后会举行庆祝晚会的露天剧场。游行自愿参加,无需提前报名,没有严整队形,亦可随时离开,然而茫茫人海依然一眼望不到尽头——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在同一天里见到过这么多人。

游行盛况
被裹挟在时不时开始自发高呼“卡布斯万岁”并高唱国歌的人群中,忽然感受到了一丝魔幻,似乎穿越了几十年的时光又或挪移了空间,窥见了故纸堆和游记里描绘的情形。又莫名好像有哪里触动,仿佛这就是君主制的注脚。

当地同学自豪地表示,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作为极少数受“阿拉伯之春”波及较小的国家之一,阿曼上下一片祥和,经济欣欣向荣,旅游业蓬勃发展,民众安居乐业。热情的校车司机邀我到他一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和整个大家族一起共度周末,从而让我第一次有了到阿拉伯人家做客留宿的体验,还被科普了手抓饭的正确吃法。上面提到的那位同学土豪般地带我们兜风游览各处名胜,每次烧烤生火时都要演示“火上浇油”的技能。一位中年出租车司机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卡布斯治下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日常说起苏丹也是一片溢美祝福之词,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自信。
曾遇到过一批传统的叛逆,一群英语极为流利的姑娘讲起她们的毕生梦想是定居国外走得越远越好,还有人为即将去澳大利亚念书兴奋不已,因为这样就不用再穿戴那些“愚蠢的头巾”和“冒傻气的黑袍”。一个姑娘表示自己在专制家庭中浪费了大量青春伪装自己是个穆斯林,其实每次和大家一起假装礼拜时都在腹诽。还有小哥一脸严肃地问我们:“你们相信同性恋有生存的权利吗?”然后大方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如果被家人知道他会被亲生父亲谋杀。
当然还有暗流涌动不宜公开讨论的继承人问题。作为一位已经75高龄、在位四十余年的领导人,苏丹本人于近四十年前离婚后未再娶,没有儿子(坊间流传有其它原因,考虑到文化背景会十分有意思),其他皇室成员由于缺乏历练显得能力和威望不足。于是不管继任者是谁,都要经历合法性认同的难题,何况卡布斯还是那么一位深入人心的前任。

王宫
想来还有其它一些零碎的片段,比如周末跑到十几公里外的男生宿舍包饺子,和俄罗斯姑娘兴高采烈地讨论哈利波特福尔摩斯和神秘博士,不大会英语也不会阿拉伯语的加蓬室友比比划划地带着初来乍到的我熟悉周边环境,韩国妹子惊讶于我对基督教典故的了解,来自伊朗的一群博士生有次拉我帮他们从百度文库上下载免费文档(天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资源,又是如何对着天书一般的中文页面一个个试过了所有能点的地方)并邀我共度伊朗新年作为回报,当然还有沙漠之行的日出日落,和每次烈日下跋涉的炙烤。
有时觉得无需惊心动魄也挺好的。

作为本科时代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文收尾的这一刻,忽然想起毕业论文终于写至后记的那个深夜,大学四年往事种种在心头浮现,有些印象深刻,有些我本以为早已忘却。感慨于这次自己真的真的是要毕业了。
时常会庆幸自己学了阿拉伯语,让我的目光投向之前未曾流连的方位,让我走过从未想过踏足的土地,让我遇见不一样的人,开启从未预料的人生。

作者于卡布斯大学
